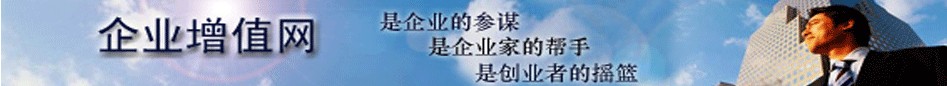|
我童年最深的记忆不是饿,而是父母的眼神。父亲任摩逊,一个满腔热血的知识分子,在纹隔时被扣上高帽、满脸漆黑地被推到大街上批斗。母亲程远昭,一个高中毕业的教师,为了养活我们七个孩子,去抬土方、修铁路,半夜还在补衣服。
我恐惧的,是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践踏,是家人的生存毫无保障。这两种恐惧,后来变成了华为的两个潜意识:
第一,必须尊重知识分子,给钱、给荣誉、给平台;第二,公司必须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尊严。我渴望的,不是富贵,是“改变”。改变家庭的境遇,改变“中国人造不出好机器”的断言。在重庆读大学时,纹隔爆发,我偷偷“扒火车”回家看望被打倒的父亲。
临别时,他把自己的翻毛皮鞋塞给我,说:“记住,知识才是你穿不破的鞋。”他自己却要光脚在泥水里做苦工。那一刻的愧疚和心酸,让我对“知识改变命运”有了近乎宗教般的信仰。所以华为可以亏钱,但研发投入绝不能省,这是给全公司穿的“知识之鞋”。
02 很多人说我既“大方”又“抠门”。这矛盾源于我的经历。
我对研发、对客户服务、对优秀员工可以一掷千金,这是对“知识”和“价值”的大方。但我见不得浪费。华为内部流传我批评员工浪费薯条、自己打车坐后排的故事,这都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每一分钱都是青春和生命换来的,浪费它就是浪费别人的生命。
这种“抠”,是对劳动的敬畏。我的人生有几个差点沉没的时刻。第一次“末日时刻”:1987年,阳台上的抉择。44岁,被骗200万,被南油集团开除,妻子离开,全家蜗居在深圳的棚户区。那不是我人生的低谷,那就是人生的“海底”。
晚上我在阳台上抽烟,看着父母的背影,问自己:任正非,你还能做什么?跳下去容易,但你是长子,是父亲。我拉着五个朋友凑了2万块,想的不是“创业”,是“谋生”。华为的诞生,没有英雄主义的序曲,只有生存主义的号角。
1992年,研发C&C08交换机的豪赌。公司刚靠代理赚了点钱,我决定全部投入自研数字交换机。所有矛头都指向我:“老任,你这是找死!”我在动员会上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 这不是鼓舞,这是破釜沉舟。
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深圳宝安蚝业村的工厂里,打地铺、加班,调试到崩溃。但我知道,不掌握核心技术,华为永远只是个“二道贩子”,死路一条。那一次,我们不是赢了,是活了下来。
03 第二次“末日时刻”:
李一男的出走。他是我在技术上的“干儿子”,我待他如亲子,倾尽心血培养。当他带着港湾网络与华为竞争,甚至挖走核心人员时,那种痛,是肝肠寸断。外界看到的是商战,我经历的是 “家庭”的分裂。我被迫成立“打港办”,亲手组织反击。这个过程让我彻悟:情感不能代替制度,宠爱不能代替约束。企业的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契约和流程之上,而非个人的情义和信任。这是惨痛的一课,也是华为走向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转折。
04 投资海思芯片。
2004年,公司内外一片繁荣,我力排众议成立海思,专攻芯片。每年烧掉几十亿,十年不见回报。内部说这是“无底洞”,我顶着巨大压力说:“哪怕暂时没用,也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公司的‘备胎’。”支持我的不是数据,是一种 “总要有人为极端情况做准备”的危机直觉。
2019年,当“备胎一夜转正”时,很多人说我有远见。其实,这只是因为我对“活下去”有近乎病态的偏执,而芯片就是生存的“氧气瓶”。建造华为这台机器,最难的部分是改造我自己。最关键的“零部件发明”:写《华为基本法》。
1996年,公司大了,我说的话开始被当作“圣旨”,这很危险。我意识到,必须把个人的思想转化为组织的共识。
我们用了三年,八易其稿,吵得天翻地覆,终于弄出这本“公司宪法”。它的核心作用不是管员工,是用来管我自己的——让我的权力受到约束,让公司的方向不因我个人好恶而漂移。这是我把“人治”关进“法治”笼子的第一次尝试。
05 向IBM“削足适履”。
1998年,华为病得很重:交货慢、浪费多、部门墙厚。我邀请IBM来改造,花费相当于公司一年利润。改革触及所有人利益,抵制声浪滔天。很多跟我打天下的老臣哭着说:“老任,我们当年这么打胜仗的办法,为什么就不行了?” 我最痛苦的决定就是:向自己创造的过去开刀。我在干部大会上说:“谁抵制变革,就离开华为。”为了活下去,我们必须先否定自己,穿上“美国鞋”,哪怕血流满地。这场革命让我明白:创始人的胸怀,就是企业的天花板。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否定自己的过去,企业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
06 不能让雷锋吃亏。
我见过太多奉献者被辜负。所以在华为,绝不让奋斗者吃亏。我们设计了一套“获取分享制”,你的奖金不是上司定的,是前线打下来的粮食,按贡献自动分。我们要让“拉车的人”比“坐车的人”拿得多。这套简单的逻辑,把几十万人的私心,引导到了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公道上。这才是组织最大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