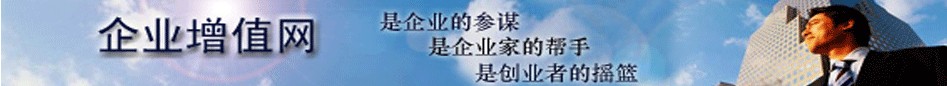|
美国霸权时代正在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世界秩序,而界定这种秩序的是大国竞争和高涨的民族主义。这一转变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这种新环境将意味着过去30年推动全球增长和发展的独特条件不复存在,或者至少会背离那些独特条件,并会带来日益复杂的系统性挑战,而这些挑战需要新型技术、创新和协作才能解决。
简而言之,技术和企业要在这个新时代蓬勃发展,需要比以前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耐心和更高的管理水平。为了打造和支持下一代经久不衰的企业,我们需要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来建设企业,一种超越并最终重新定义风险资本的方法。
再全球化的兴起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标志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的“历史的终结”,意思是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各国最佳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争论宣告结束。不久之后,苏联的解体再次确认了美国身为世界上唯一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角色。此后近30年里,世界经历了极其罕见的事情:没有大国竞争。这导致世界上许多地方采用了美国的政策偏好——自由市场经济与贸易、民主政治和开放的技术平台。这些发展助长了巨大的全球增长,致使各国为了追求经济繁荣而不再优先考虑其国家政治利益,这种现象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称为“黄金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
这一时期的自由市场改革、全球化和技术转型还起到了降低价格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这些力量,以及世界各地普遍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个环境有助于推出新的、能够刺激创新和增长的金融产品。对于私募股权、甚至风险投资这样的行业而言,购买、再融资和出售资产的能力成为了强大的利润倍增因素,它甚至可以让边际投资产生强劲的正回报。在一个原本低产的环境中,这些回报吸引的投资上了新的台阶,也吸引了大量资本,助长了新一代的企业和技术。
然而,像所有的假期一样,世界的“历史假期”已经结束。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减弱,大国竞争正愈演愈烈——最明显的证明是中国的崛起,但也有像欧盟这样的区域集团以及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国家。
与此同时,全球危机的影响及其更加频繁的程度,让一个紧密关联的系统的关键弱点暴露无遗,该系统更加倚重开放和速度而非安全和稳定。东亚金融危机、科技泡沫的破灭、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全都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动态的全球化世界具有的风险,而在这样的世界上,局部事件会迅速变成全球性危机,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
随着世界各国力图从这些挑战中恢复过来,并保护自己免受下一次挑战的冲击,也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各国的目光开始超越经济和全球效率,重新将国内政治和全球应变力放在首位。这种行为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英国脱欧和移民控制到经济制裁和供应链回流。
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种转变将导致一段时间的去全球化——各国试图消除过去30年的所有相互依存关系,以加强自己的国家体系——但这种预测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依赖全球化来支撑其国内产业。比如,墨西哥和德国的贸易在GDP中的占比都在80%以上,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25%。
现在完全解除全球化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不得人心。不过,对国家政治的重新关注会使其采取不同的形式:再全球化的形式。在再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各国会寻求在全球化的好处与在其最复杂、最具系统重要性的行业中建立更具独立性和应变力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这些行业包括:医疗、国防、能源、制造业和金融服务。此事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耐心,因为各国和各企业都希望加强和重新构建自己的国内研发、制造和分销网络。这些挑战的深刻本质要求使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进行企业建设和创新,从而改变风险资本本身的模式和性质。
超越风险投资
在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时代,我们似乎是在走向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数字的东西支配着实体,技术通过无拘无束的市场轻易在全球扩散。这些条件,加上低价格、低通胀和低利率的相关好处,导致了新形式的金融工程,使资本成为一个杠杆点,并让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的预示纷纷应验。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现代风险投资业诞生了。当技术寻求将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进行数字化时,企业能够获得相对廉价的资本,为未经验证和不赚钱的商业模式提供资金。这种数字化的资本和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而且在面对经济进步的时候,由于政治干预有限,机会似乎层出不穷。为了利用这些动力,技术和创新有“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的倾向(如果算不上意图的话),而风险投资成功的典型特征是快速扩大规模、快速退出、高回报和有限治理。
相比之下,在这个再全球化的新时代,技术将被用来解决远更复杂、高风险的结构性挑战,没有无拘无束的市场、低利率和“轻松赚钱”的好处。这将需要一种新的风险投资模式,即支持更大的资本承诺、更长的投资期限、更高水平的合作以及更大程度和深度的管理。
再全球化的复杂性及其对未来企业建设的影响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中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在新冠疫情让全球供应链的弱点暴露无遗之后,美国宣布计划投资2800亿美元来加强其国内的半导体研发和生产能力,并对先进的半导体资源实行一系列的出口限制,旨在加强和维持其竞争优势。
欲对这一复杂产业实现如此雄心勃勃的重新构建,需要的不仅仅是创建新的、技术先进的美国企业,使其能够迅速大规模生产先进的芯片。它还需要大量的资本,以及与政府机构和现有工业企业的合作,以完全重组供应链——从研发到组件材料和制造,一直到分销和贸易。
应对这些挑战的新企业诞生的时候,其雄心抱负、商业模式和分销网络的水平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完全不同,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无法在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内衡量出来。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这些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并非半导体业所独有。在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疫苗短缺的影响和不堪一击之后,许多国家现在正努力加强其国内生物技术研究和生产能力,以使他们不必依赖他国的成功和大度来保护自己的公民。在任何国家,要通过建设、甚至加强国家生物技术产业来创造这样的全球应变力,这需要数量庞大的开发,而且会耗时数十年时间——远远超过当今风险投资模式典型的十年基金寿命。
此外,在全球日趋紧张的经济环境中,随着应对此类挑战的融资需求不断增加,技术需要提供的杠杆作用是金融工程和政府资金无法再承担的。投资的速度和规模要求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企业和现有系统合作。以能源为例:去年,英国和欧盟政府宣布了一系列紧急能源补贴,以应对因乌克兰战争而导致的能源成本上升,致使此类措施的总成本超过5000亿美元。然而,随着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各国根本无法再无限期地承受如此规模的财政支持。曾经在一些领域,融资可能有助于支持国家能源应变计划,现在技术必须在这些领域承担更大的效率和影响。
美国的医疗服务也是如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患病人数增加、再次出现全球疫情的风险隐现,以及资本成本的增加,私营企业和政府都将无力花费数千亿美元进行新药开发,也无力继续为无利可图的医疗模式提供资金。针对药物研发、基础设施与支付系统以及数字医疗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这将是在这些复杂、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大幅扭转成本曲线的唯一途径,而变革发生的规模只能根据现有系统的资源与合作关系需得到多大程度的利用而定。
虽然再全球化的挑战需要新的融资和合作模式,但考虑到这些挑战的深刻性及其对人和社会的潜在影响,它们最重要的影响涉及的是风险资本家必须承担的责任水平和治理深度。随着我们寻求建立下一代防御系统、分散式的金融网络,并在过去让人类推理和判断的领域利用人工智能,这一责任变得愈加紧迫。
在过去,更有限的资本要求和更短的投资期限令人遗憾地让投资者放弃了治理和负责任的创新计划,将其交给管理团队,或者把这些问题完全推给其他投资者。这在社交媒体上以及环境可持续性方面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抑制了包罗万象的繁荣。展望未来,这种新环境的挑战需要更长久的投资期限和更高水平的金融、智力参与,从而使我们与结果更紧密地协调一致,并迫使我们更积极地管理那些我们致力于创新的技术、系统和企业。
投资的新时代
在过去的30年里,风险资本既是快速创新的促进者,也是快速创新的受益者,而这种创新是“经济高于政治”时代的特征。整个行业的参与者已经开始期待一个普遍有利的风险/回报权衡,其典型特征是在需要有限管理、相对短期的投资中获得高回报。然而,在再全球化和全球应变力的时代,这些模式不再足够。当今挑战的复杂性及创新影响的严重性必然需要一种新的投资模式——这种模式会优先考虑更大力度的合作,并用更长远的思维来打造经久不衰的企业。这不应该成为消极悲观或感怀“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的理由。在这种新环境下建设企业会确保持久的成功。如果风险资本能够拥抱这个时代的新挑战和新机遇,并将其当成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机会来重新构建世界,那么风险投资将继续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