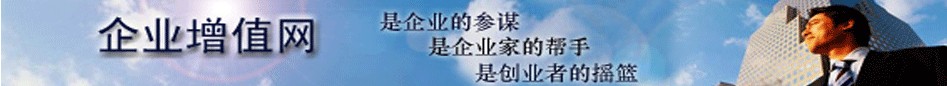|
美国肯塔基州的马类公园,立有这样一句碑文:“人类的历史是在马背上写下的”。中国人中间也流传着“马上得天下”的种种传奇故事。自从蛮荒时期以来,人类为了自我保存,改善生存状态,就开始了漫长的驯服自然的过程。驯服野生动物,去除其野性,便是早期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实际上人类摆脱对马的依赖不过刚刚近百年的时间。即便如此,在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马仍然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生存工具。人类文明的另一个成就是对狗的驯化。如果所有的狗至今仍是野狗或狼,草地上的羊群和屋舍里的财产不知道要遭受多大的损失,那些与狗为友的人不知道又会平添多少的寂寞。没有犬马之劳,人类的文明不知道要打多大的折扣。
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对野生动物的驯服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已有了大量的记载。但是与这一进程同步进行的另一个进程,即人类对自身的驯化,所受到的关注则少得多。人类的文明化过程是逐步脱去作为野人的野性变成文明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远比人类对动物的驯化重要得多。因为一个社会,不论它把动物驯化得多么好,只要这个社会成员自身的野性未脱,这个社会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文明社会。
人类为了驯服自己身上的野性可以说是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发明了种种方法来使自身趋于文明化,其中的手段包括伦理、法律、监狱、学校等等。统治者与政府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统治者和政府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暴力机器、教育机器和宣传机器对社会的普通成员进行没有休止的惩罚、授受和灌输。特别是,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与政府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的强制。让政府用暴力的手段来压制野性在政治学中被称为是“野蛮的发现”。这就是说,人类为了提升自身的文明程度,动用了一个野蛮的工具。于是,当人们成功地找到了驯服被统治者身上的野性的途径之后,人类被一个更大的、空前的挑战所困扰:如何驯服自己的统治者?统治者及其操控的政府的确是统治和驯化普通民众的有效工具。可是,无论被神化到什么程度,统治者和政府成员都是凡人。统治者用政府约束凡人的野性,可是,一旦治人者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历史上,无数事例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
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除暴力之外,最有力的武器不过是最无力的道德说教。对不中听的说教,统治者们轻则像齐宣王那样“顾左右而言他”,重则像纣王那样让比干剖心而死。
在人类的五千年文明中,在驯化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很不均衡的。对动物和人类普通成员的驯化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全面完成。对普通民众的驯化也早已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对统治者的驯化则进展缓慢。人类驯服了自然之后,更为紧迫的任务就是驯服人类自身。对统治者的驯化,只是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普遍的效果,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到了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宪法与以往任何法律的区别就在于它是限制统治者和政府的专横权力的法律。在无宪政的社会中,法律通常是统治者束缚普通民众的工具,而对统治者自己则鲜有束缚力,基本上是无效的驯化工具。
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便是宪法。其中的特殊材料,包括对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和保护、对统治者与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纵向与横向的分权与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法律高于统治者意志法律理念等等。可以说,宪政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最重大的里程碑,因为它给人类所面临的最大课题:驯服统治者,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自二千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自由民主政体的民主化浪潮,这样,人类在政治文明领域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与宪政法治在西半球结伴而行,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驯服统治者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把那些挣脱法律与伦理的羁绊、用专横的权力为非作恶的“统治者”送交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这一“殷鉴”是任何想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后尘的统治者们所不能熟视无睹的。
19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给各国统治者的行动划上禁区,不仅拒绝让统治者进入个人享受自由与权利的领域,而且规定统治者有义务保护个人的这些自由和权利。是否承认并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已被看作各国是否接受人类文明基本准则的一个重要尺度。闵主县政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二十世纪有了更大的发展。它们走出了西半球,在经历了三次闵主化浪潮之后,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扎下根来。
直至今日人类的全部进化历史表明,人类既离不开统治者,又不能不驯化统治者。统治者对人类的必不可少早在前人类的猿猴时期就已是命定的事实。一部人类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猴王”到人王的进化史。灵长动物学研究表明,现在像猴子、猩猩、狒狒、长臂猿等灵长动物都过着人类的祖先曾经过着的那种群居生活。大多数灵长动物的社会是围绕着一个可以称为首领的统治者而组织起来的。如猴子就是围绕着“猴王”来结群生活的。这样的首领通常至高无上。灵长动物社会的本质就是在首领的暴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的建立消除了自相残杀。人类社会中的政权最初也可以追溯到那个作为“君王”的统治者身上。由于不必再把精力浪费在自相残杀上,整个群体就能致力于合作性事物——采集食物和保卫地盘。这样,也就迈开了走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第一步。
然而,靠暴力建立起来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从猿猴社会到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都历来如此。猴王权力的更迭即便是流血的,却不大可能是致命的,更不会残害无辜者。而人类社会中行专制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这种政权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猿猴过专制生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存机会,而现代的专至郑权是要最大限度地剥夺人类的生存机会。如果不能成功地驯服,“人王”比“猴王”要野蛮得多。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之所以可怕,正是因为他掌握的是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而且,越是专横的统治者越是想取得对暴力机器的彻底控制。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大行其道,就是因为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在民主政治下,权力不仅应该分享,而且应当被用来尊重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因而应该受到制衡。对领导人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不同政体文明与否的尺度。
一个民主政体就是统治者被彻底驯化的政体。从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中受益的首先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统治者们也同样从中受益莫大。在民主政治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舆论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在历史上,统治者们的身家性命从未比在闵主政治下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所以,从对统治者的驯化中受益的应该说是全人类。二十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人类对其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不可逆转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标志就是自由闵主的确立。
时值二十一世纪的前夕,有一点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凡是专横的权力肆虐的地方,文明就势微,野蛮就当道,人民就遭殃。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繁荣的经济。不是闵主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发达的国家;专横权力横行的国家不应算是文明的国家。
鉴于今天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国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用民主政治来进行统治者驯化,可以预料,二十一世纪将是在全球范围之内驯化治人者的世纪,因而也是民主政治取得全面成功的世纪。这可能意味着人类文明得以摆脱以杀戮和迫害为特征的不彻底的文明,把文明阳光照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文明在于驯化,二十一世纪的重点将进一步地落在统治者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