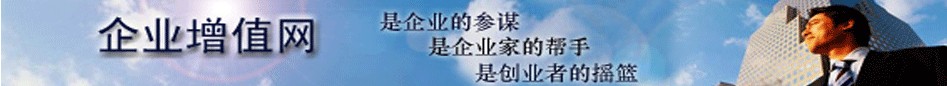|
记得第一次跟马云握手,的确有遇见了E.T.的惊诧。那只手绵柔无骨宛若妇人,继而轻轻地有力一执,如绵里藏铁。后来听一位懂手相的说,这是大异之相。
大异之人能否成大异之事,取决于三点,是否身处大时代,是否投身大行业,是否成就大功业。马云何其幸也,居然三者俱得之。今天是马云的生日,也是他创立阿里巴巴二十周年。在这里,以薄文道贺,并试图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马云到底是不是“外星人”?
1
马云接触互联网是在1995年,是当时最早触网的几百个中国人中的一个,这些人里迄今还活跃着的包括马化腾、丁磊、雷军等,与上述几位相比,马云是唯一不会写代码的。在四处碰壁多年后,1999年的9月,马云在自己的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10个月后,他成为第一位登上《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
这背后有一个宏大的产业图景:在经历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朱镕基总理为了拯救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对民营企业开放进出口业务,从而引爆“中国制造”的黄金年代,阿里巴巴正好赶上这趟大车。其实在当时,在同一赛道的企业多达数百家,而唯一大成的只有阿里巴巴,马云要感谢他爸爸把他生在了浙江。这个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小省,却有全国最多的专业市场和最活跃的中小制造企业集群。
阿里巴巴最早的对标模式,并不来自美国硅谷,而是浙中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用马云的话说,“阿里巴巴是网上的集贸市场,也就是网上的义乌”。阿里是真正的“中国式胚胎”,诚信通、中国供应商和支付宝,俱是原创性创新。阿里的销售队伍被称为“铁军”,这个名词的背后其实是一部血泪史。
在很长时间里,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销售人员要把虚无缥缈的“网络信息服务”,以几千乃至数万元的价格卖给几乎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农民厂长们,靠的就是“连哄带骗”和死缠烂打的铁军精神。
如同所有伟大的公司都不来自一个既定的“蓝图”,阿里二十年,也是一个随时运起伏的二十年。这其间,呈现出的是一条波浪式增长曲线:它在2002年创办了淘宝网,涉足网上零售业务,2013年推出余额宝,染指互联网金融,2015年创建菜鸟物流并尝试跨境电商,2016年提出新零售和大力投入大数据业务。
每一条增长曲线的背后,都意味着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而它们之间既有业务关联的可能性,又没有互为成就的必然性。阿里的不可捉摸和无所不在,在中外商业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2
阿里的成功,大而言之,得益于两条,一曰“工具迷信”,一曰“大水库模式”。有很多做制造和零售的企业家,对马云一直很不满,觉得是他夺去了他们的生意,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阿里对实体经济其实没有贡献,因为,“它不就把货物从地面搬到了网上而已嘛”。这样的认知,是他们被淘汰的根本原因。
世上所有商品交易的成本和获利,都取决于三点: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渠道的多层级,三是资金的流通效率。互联网的所有能力恰恰都在于对这三点的破坏性重构。马云对互联网的工具能力始终有一种宗教般的迷信,它似乎不是建立在可行性的前提下,而是“非如此不得活”的坚决心。
2014年,马云对银行业喊话:“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这在当时的金融界溅起一片不忿,但是仅仅三四年后,再没有人对此稍有异议。在很多时刻,马云的商业判断,大多不来自知识,而来自洞察,除了先验的“工具迷信”,这的确是很难解释的。
十多年前的2007年,受阿里巴巴集团的邀约,蓝狮子曾经派出两组财经作家进入公司实地调研,分别长达半年,出版了两本书籍,一本是《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一本是《淘宝网:倒立者赢》。
那时,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是B2B,刚刚收购了雅虎中国,淘宝网的当家人还是被称为“财神”、喜欢收集烟斗的孙彤宇。
在一次交谈中,马云问我:“世界上最好的生意是什么?”
未等我回答,他很得意地给出了答案:“是办一个国家”。
“你看,国家就是圈一块地,养一堆警察,建立一种秩序,然后,在这里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向你交税。”他稍稍提高了一点声量,“所以最好的企业就是国家模式。我建一个大水库,把管子接到每户家庭里,你一打开来,我就有钱赚。”
2007年的阿里巴巴显然还不是一个“大水库”。但2019年的阿里巴巴绝对是“大水库”,而且不止有一个“大水库”。很多年后,我写《腾讯传》,常常比较这两家企业的异同,它们的成功都是“国家模式”,或者说“大水库模式”,不同的是,腾讯至今只有社交一个“超级大水库”,而阿里起码已经建成两个:电商和互联网金融,并且很可能在物流和大数据领域再造出两个。
在公司成长范式上,腾讯是进化出来的,从QQ到微信,其内在的基因逻辑是一致的,马化腾以“流量+资本”的战略,把护城河直接挖成了天堑。而阿里不符合进化论,它是突变出来的,或者说是被一再想象出来的。
想象就跟逻辑没有关系了,在本质上,它属于艺术的范畴,在商业世界,唯一可以对应的概念,是企业家精神。
3
再来说说阿里的企业文化。我认识很多阿里人,他们都很不“精英”,如同一把被不起眼的麻布包裹着的名刀。这家公司看上去很江湖,甚至有点散漫。比如早年的阿里,每个会议室用的都是金庸小说里的地名,光明顶、黑木崖、灵鹫宫等等。每个阿里人都要起一个“花名”,金庸十五部小说中稍稍正面一点的人名都被抢光了,除了韦小宝。
不过你仔细想想,当每个人都开玩笑地把爹娘给的名字隐去,其实内在的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类宗教式的价值观重塑和人格再造。马云不懂代码,不爱开周会,厌烦看财报,所以,他只能散财聚才。在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里,阿里的利益分享机制是最慷慨的。马云说,“员工第一,客户第二,股东第三”,这个公式在商学院的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
比较腾讯与阿里的主业,前者涉足的行业分别是网游和社交广告,这两个行业加起来的市场总规模为8000亿元左右,而后者所涉足的零售业务市场规模为40万亿。因此,阿里的行业相关渗透性要高出很多,围绕其生态可独立创业的机会点便也更丰富。
这就构成了一个现象,在阿里的周边如丛林般地生长出无数的关联性创业公司。阿里的淘宝总部在杭州西部的余杭区,在大楼建成前,它的对面有一个海创园——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园,常年空旷得可以长草。淘宝大楼建成后,两年时间里就挤满了创业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从马路对面跑出来的前阿里人。
与京沪深相比,杭州市的大型公司数量根本不能相比,但是,在胡润提供的中国十亿美金富豪榜上,北京有103位,深圳有77位,上海有66位,杭州有38位,列第四,其中最大的原因是,阿里系的造富能力。
二十年间,马云在阿里扮演的是CIO的角色,这个I不是Information(信息),而是Imagination——想象。
敢于想象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爱吹大牛。“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解决一千万农民的就业”“做一家活过102年的企业”,每一句都像极了一个大牛皮。马云的口条独步汉语世界,岂止生龙活虎,简直起死回生。
不爱吹大牛者,无以成大事。一个牛皮轰隆隆地吹出去,要么成笑话,要么成神话。马云说,人总要有点梦想,万一实现了呢。为什么马云吹过的牛皮,竟然大多数都实现了呢?
我没有研究过阿里的决策人机制,是马云独裁制,还是民主集中制,或是投票裁定制?不过,彭蕾的那段话可能是真实的,她说:“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正确的决定。”
阿里的波浪式增长曲线,每一条都有可行性,但是,每一条也都可以被证伪。决定其成败的,与其说是战略的英明,不如说是价值观认同和强悍的执行文化。
4
马云出名后,杭州电视台从片库房里翻出了一条很旧的新闻。在1995年,电视台做了一个路人测试节目,编导找来五六个大汉在马路上撬窨井盖,测试是否有路人制止。结果,那天晚上经过的行人们都视若无睹,直到名叫马云的杭州市民出现。
马云自己回忆说,那天,他骑单车去上班,看见几个人在抬窨井盖,似乎是要偷去卖。想要去制止吧,考虑到自己小胳膊小腿的打不过人家,于是前后跑了四圈,结果没找到路人或者警察帮忙。于是,他就一脚踩在地上,一脚踩在单车脚踏板上,做好逃跑准备之后,一手指着大汉们喊道:“你们给我抬回去!”
这个细节似乎很符合马云的性格。他是懦夫中的勇者,勇者中的懦夫。他有改变世界的好奇心,但秉质上,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样的人,有超乎平常人的勇敢,挑战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深知自己的能力边界,随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所以,别看马云天马行空,其实,即便在一个革命者的队伍里,他也不会是格瓦拉。
企业家都不应该是格瓦拉。二十年来,对马云的称呼有三变,一开始是马总,后来是马老师,近几年成了马先生。只有对汉语敬词有研究的人,方能品味出其中微妙的递进。如果你问我,近二十年间,全球思想市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知识产出方式的变化和知识权力的让渡。
在很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同为社会精英阶层,前者供应观念,后者供应财富,他们的社会功能很少交叉重叠。
但是,信息化革命改变了这一格局,它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世界推平,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对人类行为及公共治理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由此所产生的专门知识,对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和获取能力,提出了致命性的挑战。
知识世界的地理疆域发生了微妙的大挪移,处在变革最前沿的企业家突然成为了新观念的提供者。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不再需要经由知识分子的“转述”,而直接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独立及碎片式地发布。他们在商业领域中的创富和知识能力,被普遍化为各方面的优秀智慧或美德。
在美国,最典型的代表是乔布斯和巴菲特,在中国,则是我们的马老师或者叫马先生。对于这一被迫披挂上的角色,在一开始,马云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有一段时期,他经常会发表一些听上去有点“反智”的言论。比如,他对名牌大学毕业生嗤之以鼻,他说“不读书和读书太多的人,都不太会成功,所以别读太多书”。他调侃说,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都是扯淡。他还常常跟一些神神鬼鬼的人扯在一起,前些年的李一道长和王林“大师”事件,都弄得他有点尴尬。
被偶像化或外星人化,只能带来短暂的虚荣,而更多的是无从言说的苦恼和不适应。在过往的中国企业界,王石、柳传志都掉进过这个陷阱。马云曾开玩笑地说:“人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创造了阿里巴巴。”唏嘘之间,未免不是来自于这样的身份焦虑。如果说,他给这个时代出了无数道挑战题,那么如今,他也正在遭遇一场“身份挑战”。
5
另外一个更大的“身份挑战”,是阿里巴巴本身。2013年,《金融时报》把马云评为“年度人物”,此前的当选者包括乔布斯、奥巴马等。
在接受访谈时,马云说:“就正如互联网在改写零售业,我们相信阿里巴巴最终同样会从根本上改写金融、教育和医疗保健等由信息驱动的行业。我相信一旦这种变化出现,一旦所有人都在网络上相连起来,互联网的平等和透明的核心精神将有可能让中国社会跨越一大步,发展出更强大的体制和社会基础设施。”
这段话有两层很重要的信息,其一,阿里把互联网视为工具能力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行业,它将可能赋能于所有的商业服务领域;其二,阿里将扮演社会基础设施供应者的角色。
在人类近两百年的现代化史上,企业与国家在能力的意义上,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战略级交集。马云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做一家“国家企业”,是在2014年的12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概念,也当然是一个容易被多重解读的概念。
2015年,跨境电商刚刚兴起,有一次,我随同北京来的几位部委干部去阿里考察。在阿里跨境电商部门的大墙上,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各省的商品出口交易数据快速地即时翻动,非常壮观。其时,广东海关刚刚破获一起出口骗税大案,一位阿里的同事随口开玩笑地说,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的大数据比任何部门的监管都要准确。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副部级干部,身躯微微一动。
也是在2015年5月,马云在贵州举行的首届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说:“未来最大的能源不是石油,而是大数据。”这句话当然是真理,问题是,真理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立场和角色的人那里,却可以有别样的体味——
“在我们这样的所有制国家,石油应该掌握在谁的手上呢?”
在中国一直有一种说法,“国有企业必须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不讨论此说法是否不容置疑,不过,在现实的商业世界,情况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讲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们是电力、金融、能源、通信运营商等,基本完全被国有资本集团所掌握,那么今天,民营资本集团在社交、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地产、物流及媒体资讯等领域,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这一“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现,可谓中国产业面貌和所有制改革的最大变局,而它们都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间发生的。阿里巴巴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标本。
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这一景象曾经发生在1917年到1927年的北洋时期,当时,民营资本控制了银行、证券、航运、粮食加工和纺织产业,民大政小,有人称之为“黄金十年”,有人称之为“乱世十年”。
这道题,中国从来没有解好过。
在2017年,就当蚂蚁金服高歌猛进的时候,马云突然表态,“只要国家有需要,支付宝随时会上交国家。”言者、听者、旁观者,且各自解读。阿里未来的步步惊心,显然并不全部来自创新,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身份挑战”。所以,阿里巴巴模式始终是中国式的。
6
今天,马云生日,也是他辞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日子,他才56周岁,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是黄金的当打之年。企业家是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他们的养成,大概率与天赋和修养有关。马云肯定不来自火星,但想再克隆一个出来,却也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要诞生世界级的企业,首先要有世界级的企业家,屈指宇内,能够进候选名单的,不过六七人而已。按我的看法,排在前几名的是“一任三马”,任正非、马云、马化腾和马明哲,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退赛”,都是中国商业的损失。
金盆端上,他真的会洗手而去,如风清扬般退隐江湖?他会专心去当一个环保公益者?教育从业者?马式太极拳普及者?
其实,不得而知。
在局外的我们看来,阿里这盘大棋,玲珑初开,百子待落,远远未到终局时分,以马云的气象,恐非他人可以替代。况且,他个人及阿里的双重“身份挑战”,都不是洗一下手就可以解决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If you can dream——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人生如棋,自行其是,进未必有所得,退何尝有所失。旁人所有絮叨,都仅是无关痛痒的柳下笑谈而已。
马云,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