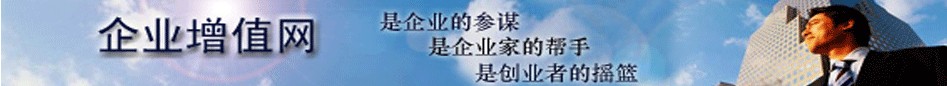|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误读
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成就进行解释,话语权却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许多错误的解读,甚至从经济理论上唱衰中国。不认清这些,就不利于我们真正找准中国实践的国情特色,也不利于我们真正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更好认识改革面临挑战和指导未来的改革。
在过去这些年来,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理论上对中国经验的解说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被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或多或少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和判断。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你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靠瞎碰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说得通俗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都还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第二是世界银行曾任的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这句话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实现的高速发展,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那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为下面的观点留下了伏笔。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唱衰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很高,而且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是,当不知道特定经济体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承认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认为这仅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导致的,只是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次性效应,很难有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称东亚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引发了“克鲁格曼-扬诅咒”。从20世纪90年代起,克鲁格曼、扬等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认为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接下来,他们又转向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四小龙一样,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林毅夫讲过一件轶事。2000年的时候,新加坡李光耀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你说我们新加坡仅仅靠高积累、高投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但我们40年来储蓄率接近50%,资本回报率并没有下降呀”。正如在这个故事中李光耀所追问的,克鲁格曼、扬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问题是持续多久才算可持续?到今天,中国经济已成功地持续发展40年。下面,我将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主动清除制度障碍,促进劳动力重新配置,进而创造经济增长的角度,分享我对上述不恰当理论及其应用的思考。
中国发展的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使用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必然要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反观中国,过去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个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仅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全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说,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正好在我们的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期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这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长。
通常,经济增长源泉可以用诸如生产函数等方法从统计意义上进行分解,等式右边包括生产要素投入和生产率提高等变量。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国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9.7%,对这个增长做具体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和扬也是主要看到的是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质资本的投入或资本的积累。
实际上,资本的积累本身也体现着人口红利的因素。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特征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撑。为什么?第一,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储蓄、积累,进而变成投资。第二,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在中国这个发展阶段上,刚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资本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扩大而出现报酬递减。事实也证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即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且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量,可以不断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也因人口红利得到了改善。
伴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还有生产率的改善,其中主要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这些年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1978-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率原则发生流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的表现,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估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10年的时期,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可以达到10%左右,而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以后,潜在增长率自然会下降,估计的潜在增长率,“十二五”期间平均为7.6,“十三五”期间平均为6.2%。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改革
我们进一步来看,40年来把人口红利从一个潜在的经济发展条件转变为真实的经济增长源泉,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其中涉及了什么样的体制改革。整个过程历时很久,涉及的范围十分宽广,我着重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重点解决的三个问题,即获得离开低生产率农业的退出权、在城乡、地域和部门之间的流动权和城市部门的进入权。
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剩余状态退出
劳动力如何从剩余状态,也就是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退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制变革任务。过去我们研究农业经济,会提到人民公社体制缺乏激励、没有效率。因为人民公社给每个社员确定一个不变的工分值,在集体劳动中计出工天数,年底不管是打下多少粮食,最后就按工分值和出工数进行分配。只要每天出工,不管干与不干,干得好与干得不好,都是不变的工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成员偷懒,对生产队的总产出造成损失,他却不会全部承担这个结果,而是由全队的人共同承担,因此许多人会倾向于不努力工作。
出工不出力也被有些学者称为一种退出方式。因为原有的激励机制无法激励人们去努力工作,又不允许实际上的退出,既不许外出打工,也不许搞资本主义尾巴的副业,唯一的办法就是偷懒,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退出方式。但是改革以后,每个农户获得了资源的配置权利,你可以自己决定干多少时间,在什么时候干,剩余的劳动力就可以真正退出来。因此第一步,农村的改革赋予了农民把劳动力退出生产率低的领域,也就是重新配置剩余劳动力的权利。
转移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流动
农民从土地上退出来了,应该和能够去哪儿?随着制度约束的不断解除,农民便从过去的“生产队社员”,变成一个有自主决策权的农户。人民公社被废除以后,农民首先从以粮为纲转向种植业乃至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得到很快发展。再后来,他们又离土不离乡,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即转移到了本地的非农产业当中。但是,一度还没有离开乡村。
之后,政府又允许他们长途贩运农产品,第一次突破了经济活动的地域界线,以及自带口粮到临近的城镇去就业,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城乡分界。再后来,粮票制度被取消,农民可以进入到小城镇、中等城市,甚至大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大量流向沿海城市居住和就业,几乎可以实现充分的流动。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最初,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可以转出来,但是转出来就只能在乡镇企业就业,想进入城市却由于没有户口,没有粮票等票证,也得不到公安局的认可,且由于国有企业尚未进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所以也不敢和不能雇用外来人口。因此,改革之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育,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城市发生的重大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城市职工的大锅饭,大批职工下岗失业。虽然一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从此之后,劳动力市场得到了迅速发育。城市的下岗劳动者想回到岗位上,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虽说他们会得到政府的扶助,但主要渠道还是劳动力市场。同时,新成长的劳动力即刚毕业的学生,也不再能够靠政府分配工作,全部要到市场上去寻职。与此相应,从农村进城的劳动力也就跟他们一起,具有了竞争同一个岗位的同等权利。
虽然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还有很多制度性的约束,无法实现劳动力的完全自由的流动和进入,但剩余劳动力通过退出、流动和进入等权利的不断获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重新配置,促进了生产率迅速提高和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创造了很多特殊的经验,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中出现的困境。虽说前苏联东欧并不具有显著的剩余劳动力,也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但是那里也有企业冗员,生产效率也比较低,因此面临改革决策时,通常就会采用两种调整方式:一是数量调整,本质上就是裁员,结果导致大规模失业;二是价格调整,也就是降低工资,这种方式虽较少造成失业,而是着眼于以价格调整的方式把冗员出清,但却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两种方式都导致一部分人在改革中受损。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式劳动力市场改革,避免了这两种方式带来的问题,总体上实现了改革开放成果的分享。
未来的劳动力重新配置
在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业劳动力的总量不断地下降。然而,官方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8%左右,这不太符合逻辑。经过这么多年劳动力市场发育,大量农民工进城,形成大约1.7亿的农民工存量,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被称作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数字上竟然显示仍有接近30%的人在农业中就业,显然是说不通的。并且,按照统计局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数据,似乎这些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果,大大不如日本和韩国在类似发展阶段上的变化,这在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于是,我和同事进行了一些估算,结合自己的一些微观调查和观察,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是显著的,那就是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其比重大幅度下降,城镇就业的人口构成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首先,估算的农业劳动力比重2015年大约为18%,要比统计数据低10个百分点左右。其次,2010年之后,城市就业虽然仍在扩大,其构成却大不一样了,城镇户籍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占比开始下降。这个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完全一致。城镇户籍人口中劳动力数量在减少,每年新增就业从何而来呢?
其实是从统计中来的。由于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计入到了城市就业统计中,保证了城市就业从数字上看仍在继续增长。即便如此,也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虽然也在城市就业,却并没有统计进来。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有多少未被统计进来,我们的城市就业在总量上已经开始趋势性下降。这是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如果说中国经济过去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人口红利,具体表现为劳动力重新配置,未来这个有利因素将消失,而且最终会成为负贡献,这会直接导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事实上,这个趋势最早在2012年就已经表现出来。
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 826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预计未来5年,人均GDP将要跨过12200美元这个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际经验,即无论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是与今后五年需要赶超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需保持继续下降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以农民工支撑的城市化的确已经后继乏力。问题出在哪里呢?从人口数字上看,中国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4年达到峰值,已经开始负增长。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就是农村每年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打工。
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其他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呢?答案是否定的。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力都已经在40岁50岁以上,以后如果没有特殊政策或投奔子女,他们不会再向城市转移。城市每年新的劳动力增量,主要就是农村16岁到19岁的毕业生们。过去两年,每年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基本上停滞,每年只增加大概30万人左右,与1.69亿的农民工存量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模拟,虽然较为粗略,但都是真实的数字。现在,每年大约有3600万16到19岁的农村人口,我们假设他们全部选择进城打工。然而,从外出农民工的数字上,却看不见任何实际增量。那就是说,一定有几乎同等数量的人在离城返乡,从而抵消了这部分人口。我们知道,40-64岁的农民工具有比较高的返乡意愿或概率,这部分人数目前是7400万,如果他们有50%左右的返乡意愿或概率,正好是3700万人,跟每年要进城的新成长农民工不相上下,相互抵消后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暂时的均衡。
中国未来如果还想保持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依靠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就意味着,上述均衡要朝着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的方向变化,即政策上要更加有利于降低农民工的返乡意愿,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增加城市劳动力的净流量,这就需要贯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户籍制度的突破性改革,让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样,就可以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大规模转移带来的资源配置潜力充分挖掘。
另一方面,越是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越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托底。作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下一步重点,资源重新配置终究要越来越集中到行业和产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劳动力的资源重新配置既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产品,有些企业会因为劳动生产率太低而退出,因而有些职工会遭遇摩擦性、结构性失业,这就需要我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革中,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设,加大社会保护的力度,从而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支撑。农民工只有成为市民后,得到更好的政策托底,才能适应这个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